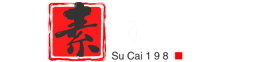在某老师荣休仪式上的发言
在某老师荣休仪式上的发言
X老师退休了,本来生日是6月18号,不过那个时候他有不能脱身的工作,回来以后又是中考阅卷和期末评估,荣休仪式一直延迟到今天才正式举行。
同事们表达与X老师共事的情谊时,X老师抢占先机,我后来评价他把最快的语速、最褒扬的语言都给了X。我常说他们语速慢,同样两个小时的讲座,我得比他们多准备一倍的内容。当然,他们深刻的思想、隽永的案例更需要回味的时间,语速慢一些自然才是合理的,只是斗嘴的时候往往容易失了先机或者落了下风,X把这解释为X老师作为兄长的宽厚,我想应该也可以算是部分的原因吧。
X的快语速和幽默而深情奠定了相对轻松的调子,中间X老师的发言还涉及到X与X老师关于喝酒的一段公案,气氛中终于没有什么感伤的味道,至少稀释消解了很多。
我第三个发言。其实我真的是做了好几天的心理建设,唯恐破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语境。前几天语文的几个朋友邀我陪X老师吃饭,我只说了一句"二十三年了"便有点鼻酸眼热,顿了一下就不再说下去,今天重提还是有点难于抑制。因此干脆不多说吧。早晨写了几句话,想了好几天了,还没有完成,郎才已尽,我也不好说能不能补充完整,先念了给大家,当时便刹住了。就是下面这四句,不成章,也不讲韵律。再接下来的话便算作这几句的"作者自注"吧:
二十三年我与君,
赏月吟风细论文。
教学探索推二有,
言欢把酒无一樽。
2001年我大学毕业,签了X市教育局教研室,报到以后分配的职责是协助赵军老师做教育科研管理。我学教育学,算是"对口"。据说那时候正在筹建X市教科所,我的工作机会就来自计划中的"教科规划办"或者叫"理论室"。最早的一个项目是和北京教育学院合作的"JIP实验",全称是"提高中学生学习质量联合革新计划"。我在这个项目里打打下手,熟悉环境。02年暑假时候,项目结束,局里领导觉得我们几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同志,不应该只在机关里"浮着",应该下沉到学校进行教学实践积累经验,11月5日我便被当时教研室的张主任送到了X八中。学期过了一半,无法安排课,就到办公室帮忙。我心里的打算是教语文,这是我从小的理想,中学时候已经比较笃定的职业选择。这一年多的工作时间里,除了和X军老师同处一室,多有讨论,其他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语文组,现在想起来X老师、X老师的确是雅量,对认识一年的年轻同事非常宽容。毕竟我小X老师24岁,小X老师14岁,都够得上忘年交的年龄差距。从他们哪里观察到或者听到的关于语文教学的理解,我希望能够帮得上。
第二学期快开学的时候,当时还在八中任副校长的X告诉我,没办法安排我教语文,问我可不可以教历史。我是来实践的年轻教师,不可能挑挑拣拣,只好答应。周五得到通知,周六日整理历史材料并备课,周一就开始上课讲隋朝史了。教语文无望,但是在语文组的"进修"没有停止,尤其是和X老师,年龄毕竟差的少些,交流就多些。而且面对文本时有很多思考的方法是相通的,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常常就是同一个文本,而文科的教学或者说教学本身,常常被学科制约住的并不多,至少不能看做差之千里,而对于教育的观察和理解就更是殊途同归了。我越来越多的进入历史学科观察,和X老师在学科间互相理解并形成共鸣。这样的讨论很多,有时候还有李强的参与。李强是我的校友,同一年来教研室,大学里学计算机,对于教育的理解,却深刻而独到,每每说出一个看法,总给我们启发。我们说他读柏拉图、读杜威,真做到了和先贤对话,有自己的理解,并不是过分的恭维,是实话。
后来X提出语文教学的一个"二有"概念,就是强调语文教学中应该在有意思和有意义两个层面达成和谐,他客气的认为在形成这个思路的过程中有体现出我参与讨论的一点价值,在一篇讨论如何开展语文教学的文章中加署了我的名字,后来申报教学成果奖时我又忝列其中,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他的鼓励更多,我写了一篇讨论某年中考题的文章,传播广泛到连累了X老师,但是对我文章中提到的问题,X老师有支持,有讨论。而此后语文中考题的一颗苹果梨引发的讨论更大,还有生物学老师参与其中,有些人以为"X的教研员喜欢吃蜜",也就是喜欢挑别人的毛病。其实"吾岂好辩哉",我们觉得学术乃是天下之公器,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不同的意见表达或许有温和有锋利,听到的人大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者正面的回应更好。总之后来我们都不怎么公开写文章批评,真是中性的评论也不做了,只是彼此之间"疑义相与析"。
X老师取得的成就大家了然,不必我多说,他的公众号所做的各种金针度人的努力,他的工作室成员所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都令人佩服。我曾经建议语文老师们把他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一个最早把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名师、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各项荣誉集于一身的语文老师,一定有值得总结的成长经验,而且我知道X老师靠的是扎实厚重的积累做到这个程度的。我认识他二十三年,依然觉得他的教研功力与日俱增,他也说累,他也说想偷懒,但是他的思考惯性总能闪现出一些非常有力量的见解,不会停止。
有个小插曲,X职称与特级评审的时候,说课环节多次遇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评完正高那一年,我这样买了一套巾箱本的《杜工部集》,里面这个奇妙的巧合。而X与老杜最相像的就是骨子里的严肃和休养里的幽默,很儒家。我们有时候用他的脸色判断一件事的难度或者他的态度(偶尔也用音量),但他很少用锋芒对别人,宁愿自己承受压力。说他谦和儒雅,是不错的。
至于喝酒,从来不是他的强项,只是我们喝酒时候的谈资,比如多少啤酒沫能让他醉酒,"喝好"的标准如何确定,和冯老师两个人喝一瓶酒的传说里他到底喝了多少,等等,当事人也没给过标准答案,当然即使给了也保不住"解释权"。不过据我们相识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推测,折算过酒的不同种类,以白酒计算,每年1两酒或许还是有的(这里是历史的),"无一樽"夸张了(这里是文学的)。X老师退休了,会不会增长几分酒量,我们当然还可以报以希望,我想停留在文学面的可能性还是大些。
赘语:
写完重读,发现X老师、X老师、X几个称呼用的很乱,直呼其名似乎不够尊重,回想起来这好像从来没有成为问题,不同的场合我们还是注意分寸的,私下里就自由多了,不过X老师的不以为忤,正是他宽厚的一个注脚。